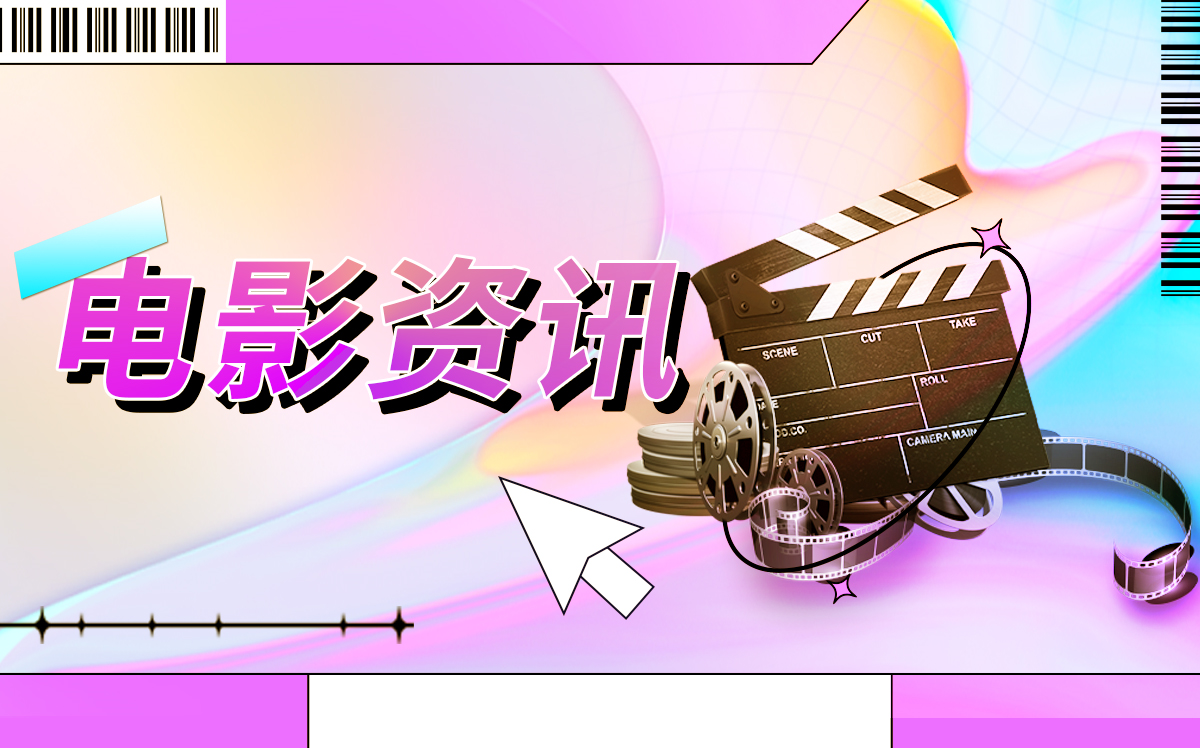 (資料圖片)
(資料圖片)
◎孫小寧(作家)
熱得出位的天氣,到底是在立秋、處暑后迎來拐點。我的新植物功課,開始轉向葫蘆科。這個季節,也是它們開花吊果時。但果實未現前,又如何辨清呢?我常覺得自己望向它們的樣子,像個呆頭鵝。“都是一個科嘛,像也是正常。”在我對著相似的藤、葉發出抱怨時,我的植物老師總會這樣說。然后感嘆,“能把一件簡單的事給人說明白,也是件不簡單的事。”習慣田野作業之人,心中自有個葫蘆科寶典,而我的目光多半落在書本銀幕上,如何讓我也明白這身邊熟物,著實難為了他。但我也不覺得我所熱衷的與這些兩不相挨,要說我這么起勁地想認葫蘆科植物,還不是因為某天見到一種像絲瓜的,想起了正岡子規的絲瓜俳。事后證明那又是一次身份錯認,卻讓我認開了真——無論如何,對著栝樓、南瓜花去念那首詩,既對不起詩,也對不起現實中的絲瓜。
正岡子規那句,屬臨終三首絲瓜俳之一,最最奇怪的是,詩已存在記憶里,往出調時,竟先是個不成俳的錯句——“絲瓜苦成佛”。絲瓜非苦瓜,何以作苦吟?唉,原來該死的腦瓜又一次篡減了意象。完整應該是——“絲瓜開花時,痰塞苦成佛。”我掐去中段,直接首尾聯上。但,錯有錯的好,這次網上重查,發現又冒出一些譯法。還看到了日文原句,以及正岡子規的詩句原帖。
以我現在的日語學習推進,拿到原句,初步可以從語言角度理解它的構成了。從音到形。原句是:糸瓜咲いて痰のつまりし佛かな。可以看到意象有三:花開、痰塞外加佛。“かな”是語氣終助詞,無實意,補音節之用。從中文角度,痰塞到佛,尚需一個語意連接,譯者正是在此做思緒的馳騁。有人也將它譯為:“絲瓜盛開時,痰塞成佛去。”但我放不下最初記下的那句。整首詩并沒有“苦”,但那畢竟是從字句里體味出的。多年之后我這種記憶截取已證明,“苦”勁兒很大呢。
正岡子規,又一個明治時代的短命詩天才。二十多歲起即咳血,終演至以病床六尺做人生的唯一場域。因絲瓜水能緩解痰塞,臨終前一年,在自家小庭園種下絲瓜。但終無濟于事。歌人西行是花開見佛,子規則是痰中見。雖然我并不想把他按在我喜歡的道人佛弟子序列。但是,想想宋禪僧那句:“維摩病,說盡道理,龍翔病,咳嗽不已。咳嗽不已,說盡道理。說盡道理,咳嗽不已。”人生即苦,可不就映現在這來回的煎熬里。
查這首詩在我微博上的初記錄,是2015年12月,儼然像在給這一整年做生命標記。那苦成佛的痰塞,首先是父親受,接著是姐姐受。姐姐本來病不在肺,但一心忙著照顧病父,父親走后才去醫院檢查,電話我的結論只兩句:“到了肺上。和咱爸一樣。”說一樣也不一樣,她并沒有像父親生前那樣使勁在咳,只是胸腔永遠有一攤瀝不盡的積水,得通過身上夾戴的管子往外抽。胸堵,氣悶,更多時是坐于床上。父逝之后的百日祭,我看到來家的每一個親戚到她床前,問候時都帶著些小心翼翼。待移到客廳,才放松開聊平常那些雜七雜八。她偶爾也聽一耳朵,嘆一句:“唉,這有啥味氣呢。”
在知“苦”這方面,她和父親一樣,都是子規的同路人。但回到詩,記憶經一次修正,反而會強化被忽視那部分。絲瓜花開,這讓我更想親眼領略它當下綻放的模樣。幾經學習與對比,我還是準確認到且拍到了它。花葉輕盈且舒展,雌花后還能見著初形的絲瓜。我有理由相信,子規眼中的花,比我看到的更美,因為這是通過臨終之眼所見。
健康人多少會驚異,病人感官與心那種異樣的敏銳、豐盛與活躍。但這恰又是事實。否則不能理解,子規創作力的活躍。量豐質優,還是近代俳句的推動者。一本《日本俳味》的詩論集讀下來,以前零零星星的讀俳感受,都被整合。借他的詩眼,又把歷代的俳人打量了一遍。子規愛柿子、蘋果、櫻葉餅與草葉年糕,這些被他寫到俳中,也是饒有意趣。這讓我覺得,這個為病所苦的詩人,苦中也飽含著無盡的豐盛。這樣的詩人,當被痰塞之苦逼到絕處,忽有明艷的絲瓜花入眼,便像是啐啄同時,定可以將人生的殘缺與完整打成一體。
如此回旋落筆時,落下一場秋雨,轉眼又快到絲瓜忌。絲瓜忌即子規忌,日子為9月19日。“子規忌”也成為其后詩人入俳的季語。語言之上再生語言,這也像葫蘆科的纏藤一般。絲瓜開花年年開,子規血啼,也可以一年年重溫下去。
關鍵詞:








